Book:城门开(北岛)
ISBN:987-7-108-03529-5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城门开》自序
因着这段序,我买了这本书,红色的封面,上面有个线描椒图把手。那红让我想起了国子监的红墙,初中总是骑车和喜欢的男生经过,夏日两边树木遮天,阴凉舒爽。很多年后突然想起那个男生给我的生日卡片上一串数字,百度过后才了解其中深意,有种后知后觉的青涩。内封是沉绿色,静静的仿佛宫阶一角的苔泥。
书买回来的那一晚,我梦见从香港回家,怎样别人也不让走,后来偷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到了和平里南口。小时候住在12号楼,通向东街有三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最北面是民旺胡同,最南面是二小的胡同,中间那一条如今已经没有了,被一个商品楼小区占了,12号楼就在中间那条胡同和二小的胡同中间,要穿过一片平房,曾经有小学同学就住在那平房里,我去他们家玩赛车。梦里面我着急地跑进中间那条胡同,忽然想到我早就不住在12号楼,于是又穿过平房跑去了民旺胡同,路上遇见一个高中同学在和人聊天,就像胡同里的人常用的姿势,聊到地老天荒一样。醒来以后忽然觉得记忆错乱,跑去问父母是不是有中间那一条胡同。
那天下午,看完了《白先勇自选集》以后就翻开了《城门开》。
北岛是四中的校友,要不是最近他写的那篇《北京四中》在网上传开了,恐怕很多人还不知道。他不像李敖,回个北京还要兴师动众地去四中;不像陈凯歌,跑回四中挑个空教室拍讲自己的纪录片;也不像冯至,有篇诗歌选在课文里,老师讲课的时候顺便提下这个校友。你在北京四中的名校友那里找不到北岛的,顺天中学堂嘛,自古紧跟中央指示。高中那时候,风花雪月,有一次周五下午,同是四中毕业的语文老师带着一群少男少女去北海划船,大家装模作样地读读现代诗,是在那样的课上,我们才知道北岛原来是校友。后来买了本他的诗集,发现老师说错了,那首叫做《生活》内容只有一个“网”字的诗是出自北岛,而非顾城。对于那个青春猖狂的年代,北岛讽刺而不加掩饰的愤世嫉俗让人读起来格外舒爽。
因此我并没有想到他的散文竟是这样沉着,人漂泊了十几年,被祖国拒之门外,这番阅历已经满足了白先勇说的作家需要的深度和广度。他父亲病危,零一年开始获准回来三次,发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不要说他在外十三年了,我出去不过四年,回来已有此感。书中点滴回忆,无不引起我许多共鸣,比如看小儿书,养鸡鸭蚕兔,有些童年游戏我虽没跟同龄小孩儿玩过,也和父母玩过,比如抓蛐蛐儿,粘知了。他提到的游野泳,我虽没在北京玩过,却曾经很多年前在漓江里游过泳,那仿佛不可踰越的逆流至今印象深刻。而游泳之流行,还有“一年级的小豆子”等歌谣,确是我儿时的经历。还有小时候在紫竹院和堂哥堂姐摸鱼,他们拿了我的凉鞋去抓鱼,结果鞋也丢了,然后俩人把我背回了奶奶家⋯⋯
那时候人小,觉得身边无尽的趣味。就像他书里提到的那样,我和表哥表弟在姥姥家漆黑的楼道里捉迷藏,自己吓自己,仿佛黑暗处能蹦出什么东西来。
还有北京的味儿,印象最深的就是下雨下雪的时候,那种新鲜的味道我在别的地方都没有闻到过。
小时候我家也住过他说的那种和另外一家共用厨房厕所的楼,就在民旺胡同,如今还能见着,有着那时特有的灰色。只不过我们那时另外一家直到我们要搬走才住进来。我记得妈妈给我洗澡的时候,抬头看见昏黄的灯泡离我远远的,黑乎乎的房顶仿佛无限高,我到现在都对白色灯光有种反感,觉得冷冰冰的,所以宿舍里装的台灯我从来不开,而我自己的三盏灯,无一例外装的都是偏黄的灯泡。那时也放炮,在楼下,都是爸爸在点,我只管离得远远的,攥着妈妈的手,也不让她过去,等着二踢脚的第二声响。至于那手执的烟花我也一向不怎么激动,总觉得火星子会沾到自己身上。学校里学跳绳,我怎么也不学不会,总是怕打着自己,妈妈只好早上起来下楼教我跳绳,那是开春的时候,满院子的柳絮纷飞,有人家的被褥晾在外面,粘上了很多小棉花。不过我直到现在,都不参加任何大跳绳比赛的,还是怕,觉得和前面的人离得太近会被打到,一定要空一个我才敢跳,人家自然是不会要我的。
我最早上的和平里六小,校门口有很多流动的小摊,卖零食和文具。我就跟妈妈说学校要交钱,然后拿来两块钱买点吃的和贴画,或者就是帮同学做作业赚钱。那时候一个小袋子装的无花果只要一毛钱,酸酸甜甜的无比美味。后来六小解散了,我们和隔壁班被分到了和平里一小,一起过去的有一个漂亮的数学老师,我直至高中时候回去还觉得她很漂亮。一小的体育课要求很严格,立定跳远要两米,我三年级,还没学跆拳道,也就能到一米三,拿个三十分。体育老师看我好玩,整天喜欢粉丝儿粉丝儿地叫我,弄得我很委屈。而漂亮的数学老师有一次穿了体育老师的背心,两个老师一起看着我们上自习,于是我连数学老师都讨厌起来。后来发现那个背心其实每个老师都有一件。
小孩儿都想住平房,觉得那儿比楼房好玩多了,据说我出生时候是住过一段时间平房的,不过我对此完全没有记忆。妈妈有个同事那时候住在民旺胡同的平房里面,她有个女儿,比我小一岁,我挺喜欢到她家玩,因为有很多女孩儿的玩具。我家就是一个房间,晚上我睡在沙发上,屋里还有架钢琴,所以是万万没什么地方放玩具的。有一次我记得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她家睡了一会儿,卧室上有个小窗户。高中演《雷雨》,读到那些窗户下面的戏,不知怎的,脑海里都是小时候见着的这个小窗户。后来才知道,那一晚父母把我放在别人家是因为姥爷去世的缘故。
北岛八岁的时候搬去了三不老胡同1号,我大概七岁的时候搬去了12号楼,开始有了自己的大房间。12号楼是个区字框的形状,中间是个花园,也有很多一楼的住家有个小院子,院子外面开着凤仙花,我也拿它涂过指甲,或者别在耳朵上。院子里有女孩子,跳皮筋,踢毽子,跳房子,递包儿,前两个到现在也不会。高中体活课,班里有女生去跳皮筋,那次机会我也放弃了,跑去打篮球了。在12号楼仍要穿过胡同去上学,中午回来午睡,时常能听到楼下弹棉花的吆喝,还有磨刀人的片儿刀扰人清梦。北岛提过护国寺的小吃,那应该是西城的地方,我们东城是去隆福寺,到处是吆喝声,后来隆福大厦一场大火,烧死一条街。那种破败,让我头一次感到了人事沧桑。
如今想想后来从12号楼搬出来以后就再也没听见过吆喝声了,小时候听见收破烂的吆喝,赶紧打开窗户喊人,或者妈妈派我跑下去,不像现在,收破烂的没事就在院子里睡觉下棋,不用怕找不着。那就是零一年左右的事了,北岛回京,我也搬出12号楼,想想北岛大了我近四十岁,但成长时所见所玩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我们和小我们几岁的孩子就有了鸿沟。记得小学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迎接新千年,那时候还离两千年早着呢,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着急麻花儿地庆祝,貌似也是和奥运有关,于是建设这儿建设那儿,如人所愿,到了新千年北京就给建没了。
我家那站叫做和平里南口,有几路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3路,13路从和平街北口出发,途径我家门口,雍和宫,北新桥,宽街,厂桥,西四,到我不知道的地方,而我十八岁之前的日子几乎都和13路有关系。雍和宫的地铁站是去奶奶家姥姥家必经之处,北新桥是离初中很近的一站,下个雪什么的就改成坐车了。而宽街是去区奥校下车的地方,从三年级开始每个周末自己坐车去上课。厂桥,那就是四中了,放学若是出门早就坐车回家,依稀记得三点四十有一辆车,售票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喜欢摇头晃脑自娱自乐。而西四,是二伯伯上班的电影院,小时候好莱坞有什么大片儿,都是坐车到西四看,如今电影院没了,高中时还在呢。而往北说,我小时候上英语课也是坐13路到北口。13路途径北海,白天时候总有很多老头老太太,刚穿上四中校服的时候是不敢不让座的,到后来一上车就睡着了,无所谓让不让座。我这次回来,仍是坐了13路到广济寺,一路上主动让座,听到那些北京大老爷们的客套,才觉得有些回乡的感觉。
我考四中也是差了两分,不过北岛那时候还没有加分一说,我是靠了英语竞赛的三分加分才险上了四中。北京那么大,小孩儿那么多,很自然的要分出个三六九等,就好像香港岛的小孩看不起九龙的,九龙的又看不起新界的。北京城八区的自然看不上远郊区县,我到如今也不太说得上那些远郊区县的方位,在我看来仿佛一锅粥一样,很远,要坐车坐到吐才能到。而城八区也有高下之分,东西二城看不上其他区,你看四中每学期校会从来不提海淀人大附,只跟同是西城的实验比比。至于东西二城之间,似乎有点谁都不服谁,东城的小孩凭着身份证上110101的开头总觉得高人一等。后来高中我从东城远走西城,渗入敌人阵营,看到班上很多同学都是初中同学,不禁有些羡慕,我的几个初中同学都被打散在四中的各个班,靠不上了。后来西城中学之间搞篮球联赛,我跟着班上女生去别的学校看球,满操场的人都不认识,这才有点身在异乡的感觉。后来初中二十二中来四中打球赛,那天我格外激动,而我唯一认识的二十二中球队的人其实是我在四中的同学,半截转走了。初中的体育老师倒是还记得我这个每次练八百米只跑四百米的偷懒鬼。北京的小孩在他乡遇上通常会问到中小学,倘若是同一个区的,那通常有很多都知道的人,但我基本上没有。离开东城以后,在东城也没混出名,西城也谁都不知道,有点遗憾。
四中的地方不错,毕竟是皇城脚下,旁边不远就是北海公园,后面是景山和故宫角楼,偶尔春暖花开的时候骑车上下学,就会特地去故宫角楼晃一圈,欣赏一下美景。那时候过家家一样谈恋爱,出了校门两个小孩儿不知道该去哪儿,于是从学校走到西单,从西单走到天安门,从天安门走到地安门,肚子实在饿瘪了,随便吃了个快餐再一起走回学校,一节晚自习已经完了。
北岛写四中的文章我囫囵吞枣地先后看过两遍,因为都是文革的事情,不是很喜欢看,文里写了一个老师自杀,拿剪刀剪了自己的喉咙,历史老师给我们上课说过,四中文革时死了的决不止这一个老师。而北岛不受四中待见,毕竟和他的立场有关:“二零零七年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我因为一块护身符,在学校一直不被老师领导们待见,所以对北岛的描述,颇有共鸣。“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可以掩盖了⋯⋯”不过我上学的时候没有文革,是一片平和。有时候听说隔壁谁谁谁出手阔绰,打听出家里的情况,几个人咬着耳朵唏嘘一声“唉”,也不知道这几个人里面有没有同样家世的人一起叹气。表面上大家相处还是非常愉快,最后也是因为阅读文化的兴趣而区别成几个小团体,而和家世无关。关于北京城八区的恩怨不过是这回事,你进了西城的学校便是西城的人,你是外地来的那就用北京话同化你,一起打球了便是兄弟。前两年回去四中,抓住一个男生说话,他满嘴的东北口音吓了我一跳,那不过是我毕业两三年以后的事,我不知道这两三年到底怎样翻天覆地,连学校里的北京话都没了。
北岛的文章还有一篇,《北京十三中》,本来我一个东城孩子,和这所学校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不过我高考却是分到了十三中。那时候高考的规矩,四中的孩子不准穿校服,因为曾经发生过穿着校服被人堵到厕所里逼着帮忙作弊。十三中的校园如北岛所说,以前的贝勒府,那种平房的教室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府学上奥数的情景。可惜四中的校舍早就现代化了,六角形的教室坐惯了,到了十三中考场见到正常的教室,不禁有些愣神儿。考试做完了,望着窗外发呆,窗外离我那么近,艳阳明灿,飞檐鸟啼,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上课开小差的日子。就是在那样古色古香的地方,遇到作文题《北京的符号》,我提笔开始写正要拆掉的德内大街,四中对着的德内大街,十三中挨着的德内大街。北岛回来的时候幸好德内大街还是他记忆中那条只有两条车道宽的路,而今已经有四五条车道了,满目疮痍。当时考场上,不知怎的,悲从中来,从德内大街写到整个北京,眼泪都滴到了卷子上,给的格子几乎写满了,远远过了八百字,只是到最后情绪也没进步起来,一悲到底。后来看到满分作文,也有类似主题,不过人家最后都扬了上去。最近看了白先勇的论文,才定了心,文章的历史苍凉是中国的文人传统,只是近代才被坏了传统。可惜当时我在考场上并没有意识到,十三中的教室成了我对北京中小学教室最后的记忆。
北岛后面几篇文章都在讲文革。有一篇《去上海》,提到外公是绍兴人,让我起了兴趣,而后面一句话便是我一直的感慨:“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爷爷奶奶支援北京,没有姥姥逃婚参军,没有姥爷投笔从戎,能有我么?其实我家还算文革中安宁的,姥姥被打成516,至今家里无人知为何物,颇有些卡夫卡《审判》的味道,总之当年不让回家,后来分去河南五七干校。姥爷带着女儿们外调西安,因此妈妈缺了物理力学的课,后来学了电子,也间接导致了我对力学的心理阴影。爸爸说小时候就是玩,中学呢就是打架,穿过胡同总有打劫的,我总感觉那时候人都变得青面獠牙起来。所以到了现在,我对大多数人狂热的东西都很反感,每次网上有个词开始流行,我就觉得那个词无比低俗起来。
一本红色的《城门开》,我看得几次热泪盈眶,因为文中那些北岛年少时和我小时候看过的北京确实没了,像我悲观的高考作文里写的,死了,死了,回声都没了。犹记当年年纪小,穿着白色的衬衫和球鞋,红色的针织连衣裙和健美裤,春日放学后,一群小不点儿在学校的花坛里攀上爬下,够桑椹,抓吊死鬼,玩甲虫,到了父母快下班的时间,跑跑跳跳地穿过胡同回家。而今,小孩们跟着保姆,坐着地铁和大人一起赶着上下班的高峰,穿过半个北京城区回家写作业,你能指望他们知道什么北京呢?历史课上还来不及哀悼没见过的内城门,皇城根也已经拆成了遗址公园,胡同夷平了一大片,雍和宫安定门的鸽群再也不见。如今我们剩下的,就是他乡听到北京话,生出无限的亲切感,赶紧一起聊聊小时候的北京,仿佛要从别人的记忆里也凑出个北京来。
我其实很感谢北岛写了这本散文,用他作家的文笔帮所有不善言的人构起了这样一座北京城。我经历过的,我父母经历过的,都让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仿佛一个记录安安全全地存放起来,不用再整天寻觅着同乡去挖掘。
“记得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
本应是感叹桃花依旧笑春风,怎知桃树也已经不见。打开一本《城门开》,晃过的只有儿时碎碎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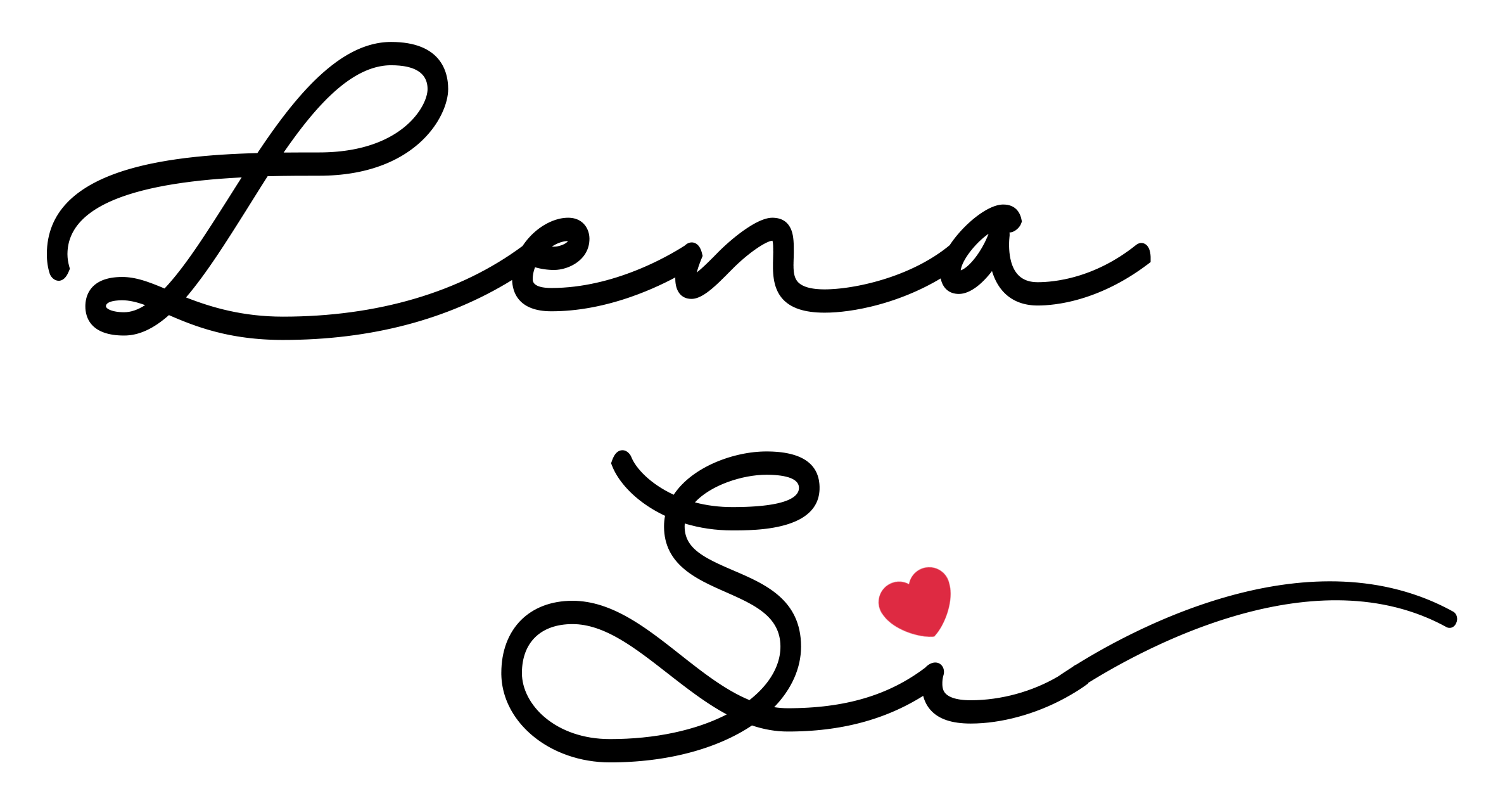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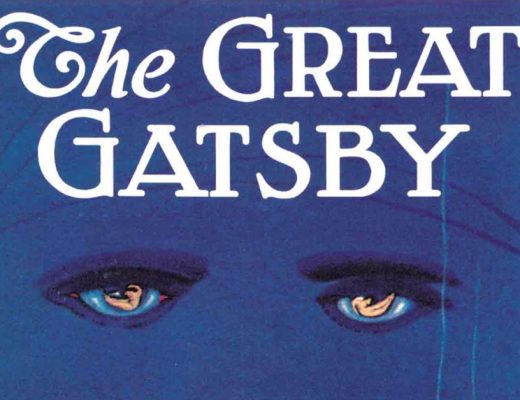


怎么对绍兴有兴趣?
祖籍
哦,那同乡。你写的蛮好,订阅了。